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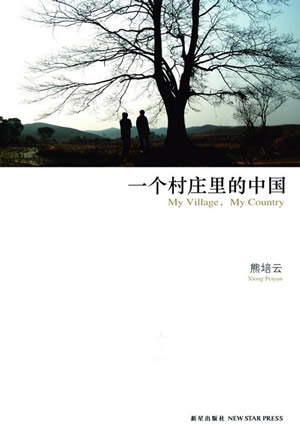
自从2000年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总理,在报纸上直言“农民真苦,农村真穷,农业真危险”后,三农问题似乎一夜之间变成公共话题,此前零散的讨论终于汇聚成强大的舆论力量。沉浸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,这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还有如此广袤的,被城市化进程撕扯得即将失去本来面目的乡村。
差不多也就是在同时,熊培云在《南风窗》发表了一篇题为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”的田野调查,“浮光掠影地讲述了当地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况与生活变迁”,引起了美国媒体对这个村庄的关注。十多年过去,随着政府免除农业税等惠农政策的实施,当年那些揪着心参与讨论的读者似乎终于获得了平静,迫不及待地转向新的话题——我们要讨论的话题确实太多,往往来不及看到彻底的解决就被迫要转向新问题——那些畅销一时的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著作也重新回归寂寞。而提着笔杆子进城的熊培云,又带着笔杆子返乡,把当年的文章漫衍成四十多万字的同名著作,时隔十年后,重新将问题带到我们面前。
与十年前不同的是,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熊培云受到法国人重拾乡村主义的启发,不再是以“发展的眼光”来看待乡村的落后问题,虽然没有在书中明确表示他认为乡村的将来应该怎样,但是从他对小堡村的历史的记述中,还是很清楚地传递出类似温铁军等力图“让乡村更乡村”的社会学家们的观点:城市的归城市,乡村的归乡村。一国可以两制,自然也可以两治。正如在谈论到村级民主选举时他所谈到的情况,对于广大的乡村而言,“依法”并不是最佳的治理方式,哪怕由于政治变迁造成费孝通撰写《乡土中国》时还普遍存在的乡绅与宗族早已不复存在,乡村失去了依照礼法自治的条件,然而乡村敞开式居住的特点始终没变,人际更加单纯,人情更加熟络,而且为乡镇精神的存在创造了空间。从“村官的抵抗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村官完全具备公正的能力,只要乡镇施加的压力不超出他们的抵抗能承受的范围,“M先生的民主理想”就完全可能实现。
和大多数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一样,熊培云关心乡村除了情感的因素,同样因为相信乡村的改变对中国的改变意义重大。只是与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不同,他并没有直接说明现状,提出备选答案,而是选择了为一个村庄撰写“村史”的方式。正如书的扉页所引用的纪伯伦的那句话所言,“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,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”,熊培云笔下的小堡村所经历的一切,都是我们整个民族曾经经历过的一切的缩影。这个国家在最近半个世纪发生的所有政治变动,都在小堡村留下了深重的印迹。
我们大多数人早已忘却的农学家董时进说过这样的话,“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,和农民的隐情,惟有到乡下去居住,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上居住。”熊培云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小堡村,并没有将这个村庄当做研究的切片,刻意保持观察者的姿态,却同样告诉了我们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,折射出整个民族的历史。
熊培云称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是一本还愿之书,愿望的起点远溯到上世纪80年代。当时还在读初中的熊培云迷恋写诗,并在学校创办了文学社,属于十足的文艺青年。有次在放学与同村农民伯伯同路,当这位伯伯问及他将来的打算,熊培云骄傲地说要“为你们写诗”。他满心期待伯伯对他的夸奖,没想到得到的却是一声叹息。回首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,熊培云不无遗憾地讲到,那位伯伯可能还是看不懂他的书,然而作为将生命托付给文字的知识分子,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观察和记录时代中的乡村,呼唤更多的人来关心农民,关心每一个村庄。熊培云的这种遗憾并不只属于他个人,然而被土地绑缚的除了中国的社会结构,还有知识分子的良心与灵魂,在真正能安心托付的乡村出现之前,这样的还愿之书还会反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(作者为知名书评人)
【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】